失联马航370乘客家属:离开亲人的日子
事发后,马航家属主要的联系手段就是微信群:
MH370失联乘客家属大群
MH370失联乘客配偶群
MH370失联乘客子女群
MH370失联乘客兄弟姐妹群
MH370失联乘客父母群
专门发泄情绪的“要亲人不要赔偿”群
北京乘客家属群
MH370家委会媒体群
“最后我问他,你知道飞机在哪儿吗?他说知道……”老张说到这里,停顿了一下,周围立刻安静了下来,附近的家属都围住了老张,等着他的下文。
老张全名张永利,白色球鞋,黑色运动裤,上身是褐色圆领衫,套着褐色夹克,留着平头,举止干练。他是顺义本地农民,大女儿在MH370上。由于长年资助一名黑龙江大庆的贫困大学生,即使MH370出事后也没有停止,因而老张在家属之中颇有威信。
“我也就没问他,飞机在哪里,”老张没来得及继续追问“飞机在哪里”,周围的人一片叹息,老张举起右手,用食指划了一条上升的抛物线,“不过那人说,你们只知道两条航线,但他知道多条航线。”老张说完,周围又安静了下来。“他有特异功能不成,要不他咋知道哪条线是真的。”一位蹲在地上的家属接口道。
老张讲述的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,在家属中已经重复多遍:今年7月,两名不知姓名的男士给他家送去了两箱舒化奶和一个信封,对老张说了上面那番话。“信封里有两千块钱,上面写着‘马行370家属收’,”老张说,“不过,不是马航那个航,是银行的行。”两千现金之外,信封里还有一些照片,照片的内容有壁虎,有鸟的羽毛。“下次,我一定问清楚飞机在哪儿。他如果说了,我就请大家吃烤鸭。”老张明显有些懊悔。
这是2014年10月10日下午5点,MH370失联后的第217天。他们所在的地方,是北京顺义空港物流园六街物流基地办公楼。这是一栋灰色的办公楼,共有五层,站在楼下,头上不停有飞机掠过。这一天,50多名MH370家属,包括老张,在与马航工作人员进行了3个小时例行公事的交流之后,走出办公室,在门口开始闲聊——这是家属最为放松的时刻。
2014年3月8日早上8点半,MH370失联。这天之后,每逢周一、三、五,这架航班上的154名中国乘客的家属们都会从北京,乃至全国各地聚集到这里,与马航人员争吵,用老张经历的这种传奇故事相互打气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,都相信自己的亲人还在人世,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恢复自由。家属们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,这个圈子里依靠两个共同的信念维系:自己的亲人还活着;所有的一切都是由马航造成的。
“我们孩子坐了你们飞机没有了,我们也不找你们打官司,你们把孩子们还回来就行了。”来自邯郸的栗二友曾经当面恳请马航工作人员——这句话最能代表这个圈子的信念。
失独:“姥姥怎么了”
10月10日这天的交流会,从下午两点开始。这是一层靠右侧门的一间办公室,大概30平米左右,六位马航工作人员坐在前排,三男三女,马航的两位年轻律师坐在左侧桌子后。20余名家属坐在三排座椅上,座椅后背上写着“马航资产”。张美玲坐在后排,马来西亚民航局官员黄惠康,这个马来西亚政府与家属打交道的唯一官方代表每讲一句,她都会小声骂一句“骗子”,然后用手不停地敲打“马航资产”四个字。
217天前,张美玲正同两位外孙等着女儿女婿的归来。她住在北京朝阳区华威桥附近的一个安置房小区,位于28层的家客厅很大,茶几前面是LG的50寸液晶电视,茶几左边墙上摆着全家的各种合影,共有三排,一共9张,除了一张女儿和女婿的合影外,其他8张都有两个外孙的身影。
两个外孙是混血儿,哥哥Peter8岁,弟弟Mike只有3岁。她家“姑爷”Muktesh Mukherjee是印度裔加拿大人,供职于加拿大某能源公司,工作地点在北京的最高点——国贸三期。
3月8日早上7点,如果一切正常,MH370应于半个小时前在首都机场降落,而张美玲应该已经接到独生女儿白小莫的电话。到了7点半,张美玲忍不住打电话给女婿的司机,让他帮忙查询航班情况,司机咨询了北京机场地勤后,回复张美玲说飞机延误,“还没起飞呢”。Mike由于起得太早,已经有些吵闹,张美玲拿出他最喜欢的《papapig》动画片,放到DVD里,安抚住了小外孙。
这时,张美玲突然接到妹妹的电话,“说飞机出事了,让我赶快看新闻。”她打开央视新闻频道,看到了MH370失联的消息。“我看着字幕,眼泪就直往下掉,Mike吓坏了,拉着我的手不停地摇,‘姥姥怎么了,姥姥怎么了’。”张美玲回忆着当时情景,双手紧紧抓住沙发套子。
从那一刻起,张美玲及154名中国乘客的家属的生活,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现年已经65岁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,自己会成为英语速成班的一员。
与记者交谈过程中,张美玲的手机不停地响起,都是向她推销英语速成课程的。“一个月10节课就要3000块钱,太贵了,”张美玲挂断电话,“现在教英语的可真赚钱,想找个便宜的口语班都难。”张美玲之前没有英语基础,她希望通过突击学习,在两个月内掌握会话能力。
“我现在听不懂Mike说话啊。”张美玲拿着手机大哭起来。Peter和Mike都出生在加拿大,长于美国芝加哥,英语是他们的母语。Mike一岁时,两人跟随父母来北京定居,就读于北京的国际学校和双语幼儿园。
MH370出事后,两人一年30万的学费对张美玲来说成了天文数字。于是,远在英国的爷爷奶奶今年5月将两个孙子接到英国抚养。
3月8日之前,张美玲本过着众人羡慕的退休生活。她的女儿女婿是加拿大公民,后到美国芝加哥定居,在芝加哥的百老汇街有一套公寓。为了带外孙,张美玲一共去了芝加哥8次,“已经可以申请美国绿卡了”。
到了北京之后,女婿公司在二环朝外大街的新城国际为其提供了一套300平米的公寓。女儿女婿,两个外孙,包括张美玲都有自己的房间。“晚上9点都回房开始休息,早上6点半全家起来,我那时的生活可健康了。”张美玲说。而现在的她,晚上两点还在上网,搜索MH370的消息。
此前,女婿每年都要组织全家出国旅游一次。如果航班没有出事,他们原计划3月29日去香港,全家的机票都已经买好。但现在的张美玲,连下楼都很少,她现在只关心两件事:女儿女婿何时回来;尽快学会英语与外孙聊天。
客厅电视旁放着一部白色的索尼笔记本,这是张美玲和两个外孙的通讯工具。“每周视频通话一次。(到英国)半个月后,两个外孙就不会讲中文了,Mike只会说姥姥,Peter说一句中文要想两分钟,我对着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口。”
外孙变成了“外宾”,让张美玲惊恐不已,甚至每次打开电脑,她都从原来的期待变成了害怕。在恐惧感的压迫下,虽然抱怨补习班的价格,张美玲最终同双井的一家英语机构签下14680元的合同,开始了五十节课的强化训练。“那是一个一对一的班,人家说这样学得最快。”她购买了各种英语教材资料,从《新概念》到《大学听力》,勤奋程度堪比面对四六级考试的本科生。
事实上,大外孙Peter在3月8日那天就明白发生了什么。“Mike一天到晚就要找爹地妈咪,”张美玲说,“我们这个老二跟他爸爸特别好,他爸爸妈妈不管到了哪里,住下酒店就打电话回来,老二就在旁边大喊爹地妈咪Comeback。”Peter则一直安慰Mike,告诉他爸爸妈妈都在一个荒岛上,很快就会被人救回来。
从某种意义来说,张美玲对MH370事件的看法与Peter不谋而合。“因为要看孩子,我3月24日才第一次去丽都饭店。”张美玲说。
对于所有马航家属来说,3月24日晚10点是他们最难忘的一刻——马拉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MH370终结于南印度洋。在丽都饭店等待消息的家属们,很多人当场昏倒,现场乱成一片。
当时,张美玲坐在第一排,她没有像其他家属那样失声痛哭,而是直接质问面前马拉西亚大使馆的一位官员。“我问你们的飞机究竟去了哪里,是不是还在马来西亚,”张美玲说,“你猜他怎么回答,他说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。我觉得他这就是承认了,飞机就在马来西亚。”
像张美玲这样的失独人群是马航家属圈子的核心成员,遭受的打击最大,多年的亲情回忆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负担。
家住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的胡阿姨60多岁,已经退休,老伴去年去世,儿子、儿媳妇和3岁的孙女都在飞机上。“孙女都要上幼儿园了,当时定下了两家幼儿园,国美第一城的21世纪幼儿园和兴隆家园的向日葵幼儿园,就是拿不定主意,早定下来就好了,就没这些事了。”胡阿姨反反复复地说着孙女。她每逢周一、三、五都要去马航办公室。经常发生的情况是,她周一晚上8点才回家,也不做饭,随便吃点,然后等待周三的到来。
张美玲最近去顺义马航办公室的次数减少了,因为用车不方便。
3月8日之前,女婿出门有公司专车,司机接送。3月8日之后,女婿的公司依然同意张美玲使用这部车,但需要提前一天预约,还不能保证一定能约到。“我也理解,人家司机也不容易。”张美玲也和街坊邻居断绝了来往,很多邻居和亲戚甚至还不知道她家出了事,经常问她女儿什么时候回来,她什么时候再去芝加哥。
这些问题让张美玲无法面对。于是,与马航热线聊天,成为她唯一的业余爱好。
3月24日之后,马航中国开设了一个服务热线,专门解答家属的各种问题。家属们有事没事就打过去,有抱怨的,有诉苦的,有痛骂的,也有像张美玲这样探听口风的。
“接电话的姑娘小伙子态度可好了,我就爱同他们聊,他们很多东西都不敢回答,所以听话就要听音。”张美玲说,“有一次,我问那个小伙子,飞机是不是在马来西亚。他不说话,我又问是不是在菲律宾,他还是不说话,最后我问是不是在新加坡,他‘嗯’了一声。所以我觉得,飞机肯定还在,就在新加坡,要不然其他地方不‘嗯’,但新加坡就‘嗯’了一声呢。”
除了打电话,张美玲的另一种确认方法是算命。
今年5月中旬,她来到北京八大处,在灵光寺门口遇到一位大和尚,自称断命精准。“胖胖大大,穿着袈裟,说是来自五台山,像个有道行的。”张美玲报上了女儿的生辰八字,和尚推算了一阵,告诉张美玲,要算的人遇上事了,受阻了,要揭开这事,最快也要到明年。“他还说当时就是阻力最厉害的时候,还说我们要吃官司。”五台山高僧的每一句都击中了张美玲的心坎,让她大为信服,“只凭生辰八字就能算出这些,看来女儿女婿就是活着。”事后,张美玲给了高僧90块钱,“再给多,就没钱坐车回来了”。
丧偶:“同情也许是善意,但只会徒增别人的优越感”
张美玲将算命的结果分享到微信群里,为大家提供了又一份精神支撑力量。
事发后,马航家属主要的联系手段就是微信群:MH370失联乘客家属大群、MH370失联乘客配偶群、MH370失联乘客子女群、MH370失联乘客兄弟姐妹群、MH370失联乘客父母群、专门发泄情绪“要亲人不要赔偿”群。由于北京乘客较多,他们还组建了一个北京乘客家属群。此外,实名投票群创建后,一名乘客只有一名家属能进入这个群,重大决定进行投票。当然,他们还有一个专门面向记者的群——MH370家委会媒体群。
“现在群里特别信算命的,至少一半人都算过。”张婧说。她是北京一所学校的老师,新婚丈夫是MH370的乘客。“凡是算过的都会在群里说,我找哪个大仙算过了,人都还在,有些家属甚至连续找了四五个算命先生。很多家属就是这样,有10个信息,就把9个不符合期待的都下意识滤掉,然后有一个半靠谱不靠谱的,就认准了。”
顺义空港物流园马航办公室的正式名称是“MH370家属支持中心”。这间办公室的右上角,挂着一张大比例尺的中国地图,上面标着各个省份的MH370乘客,女的用粉红色标签,男乘客用天蓝色标签。每次来开会,家属一抬眼,就能看到挂在那上面的亲人。
张婧每次去这个办公室都会坐在后排,尽力远离这张地图。
航班出事后,在中国律师协会的指导下,家属们成立了家属委员会,有十来个牵头人。委员会有专业分工,分成法律组,资料组,媒体组,技术组和杂项组,每组四到五人,由家属们根据自己的特长自愿参加。
张婧是马航家属委员会技术组的负责人。在家属支持中心,她提出问题的专业程度,曾让马来西亚民航局官员黄惠康大为吃惊。而她,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科生。
她没有找人算命,只是在微博上探究丈夫的下落。她关注了每一个能搜到的机长、塔台和地勤人员,然后与他们私信交流。“有些机长很热心,有些挺令人失望的。一个机长说节哀顺变,我都不知道该谢他还是……”
她遇到过一个非常支持阴谋论的机长,后者说“在高层的朋友”称“人还在,只是被劫持了”。“他说自己快退休了,已经活够了,不怕别人找麻烦。”劫持说在家属群盛行,一个家属甚至声称,从高层打听到政府已经锁定一个岛屿,正在训练特种部队,准备登陆进攻以解救370乘客。
类似的阴谋论在家属群中非常流行,受到普遍的欢迎。
“这其实就是一种幻想,家属宁愿相信一个虚构的事实,也不相信客观的事情。”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教授傅素芬说,“家属们已经跟现实隔离了,隔离开来以后他们心里可能还会舒服一些。如果回到现实的话,他必须去接受这个人已经死了,那他接受不了。他们的心理会采用一些回避、否认,这样的一些机制来让自己能够过下去。打个比方说,我们的身体如果有重大创伤,或者大出血的时候,人会休克,休克也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,来降低机体的新陈代谢。情绪也一样,当事实承担不起的时候,也用情绪休克或者失忆、否认来保护自己。”
现在,每天早上醒来,张婧的第一件事就是刷微信圈,然后开始搜索MH370的各种关键字。“搜370,马航,马来西亚,希沙姆丁,纳吉布,马航工作组,之前几小时就能看到一条新闻,逐渐变成一天,两天,十天才能看到新的消息。”工作之余,研读各类航空网站成为张婧的关注焦点:她清楚军用雷达与民用雷达的区别,她了解各类发动机的推进比,她能听懂空管的各种术语……
对于丈夫的生死,张婧的态度非常矛盾。“无论说他在,或者不在,对我来说都不是好答案,如果在的话,被劫持了200多天,他该受了多少罪啊。想想他如果在一个地方受这么大的罪,我宁可他一下子怎么怎么样。如果要说他不在的话,但我们的过去是那么甜蜜,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?”
亲人生或死的不确定,对于家属来说是非常尴尬的现实。MH370上的154名中国乘客,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未定状态。“我国民法规定,像MH370这种突发事件,只有在两年后,才能由家属启动宣告死亡程序。”民事律师方振宇告诉本刊记者。
栗二友今年60岁,来自河北邯郸农村,育有一子一女,女儿在家务农,儿子是154名中国乘客之一。此前,他的儿子在国内某个大型通讯设备制造公司上班,是家里的经济支柱。MH370出事后,栗二友一家没有了经济来源。他们想提取儿子工资卡的存款,被公司和银行拒绝,要求他们必须先出示死亡证明,然后才能办理。
“我先生也没办法定为工伤,因为工伤也必须有死亡证明。”张婧说,“没有死亡证明什么都做不了,但我宁可什么也做不了,也不希望看到那个死亡证明。”
3月8日之前,张婧是个幸福的小女人。她和丈夫去年结婚,住在北京远郊,两人对生活有着非常美好而详细的规划。“我们在北京算一个中等家庭,但是我的工作对于孩子和家庭都非常有利,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去,我们当时就已经准备要孩子,因为我和他都是双胞胎,我们想可能会生一对双胞胎,我们的床都是买上下铺的。”
“早晨起来打开窗户的时候,我们那个房子可以看到远处的山。这一瞬间,就觉得特别美好。暑假的时候,我可以进城陪他上下班。他上班,我在市里购物,或者是看电影,等他下班。我力争花完他一天挣出来的钱,然后一块回家。我真的这样想的,看到商店的标签,觉得这个钱比我们今天赚的少,我就可以买,这是很幸福的一种生活,我一直认为自己幸福。”
往昔愈甜蜜,现实就愈伤心。3月8日之后,张婧首先面对的,是来自各方的同情。
张婧是一个班的班主任。MH370出事的消息传来,她没有去上班,而第二天,孩子们的询问就蜂拥而来。“各种给我打电话,发短信,老师怎么还不来,咱们班炸锅了,各种催你的那种。我当时听不了手机响,手机一响我触电似的。在丽都的家属会场上,有记者手机响了,旁边有一个家属上去要打他,我爸爸说神经病啊,人家手机响了要打他。我当时特别理解那个家属,他和我一样,当时对声音特别敏感。”
孩子们还是了解到发生了什么,他们合写了一首诗献给了自己的班主任。“告诉我虽然你生命中少了一个人,但还有我们,你对我们那么好,上天是公平的,将来对你好的人一定会有。还有的学生会说老师你现在有钱花吗?没有钱花的话我给你,”张婧拿起纸巾,擦了擦眼泪,她没有哽咽,只是不停地掉眼泪,“面对马航官员我也是这样,说着说着就流泪,自己都不知道,抱歉。”
在家属中,像张婧这样理性的人不多。近8个月的时间并不足以让他们从悲痛中完全恢复过来。“我知道他失联后,只能做到现在的样子,我不能做得更好,我没有遗憾,他能给我的爱都给了,我能给他的爱也都给了,出事情之后我妈总说命什么的,我觉得不是什么命,就是一件事情恰恰碰到了。所以我不想别人同情我,别人同情也许是善意的,但是只会徒增别人的优越感。”张婧说。
张婧最近退出了大群,被排斥出了家属的核心圈子。因为她对亲人还活着这个信念不够坚定,在群里同人争吵了起来。
“群里有人阴阳怪气地说,有血缘关系的就是要比没血缘关系的更悲痛,更关心亲人,这让我受不了,他们指责我去马航办公室不积极。拜托,我是有工作的人。”
配偶这个群体在MH370出事6个月后,逐渐恢复了过来。他们有自己的工作,也把目光放到了未来的生活。他们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,不让眼泪浸染自己的生活。
然而,这个目标很难实现。
“因为这个飞机上大部分是男的(乘客),因此大部分配偶是女的,”张婧说,“她们经常在群里说,今天我家什么东西坏了,以前都是老公弄的,现在不知道找谁。很多家属平常上下班老公接送,自己不学开车,现在自己学开车,还要照顾孩子,还要照顾父母。”张婧说,“配偶经常在群里面崩溃,一个无线路由器坏了,就能哭得不行。哭得差不多了,才说我们家无线坏了,我不知道怎么弄,大家告诉她说把电源关上然后再打开,她告诉你说还是不行,哭得更凶了。”
孤儿:想去马航工作
10月10日下午四点,家属与马航官员的争吵依然持续。来自河北邯郸的栗二友走上前,指着黄惠康的鼻子问:“老黄,你告诉我,三艘船还要搜多久才能找到(飞机)?”而黄惠康讲得最多的话依旧是:“你这个问题我现在不能回答,我会代你呈交。”
栗二友再向前走一步,被旁边早有准备的保安拦住,然后被劝出了门外。坐在角落的王佳运看到这一切,稍稍摇了摇头。
在所有的家属中,王佳运可能是最为特殊的一位。他父母都在370上,其父还是马航中国的高管。“我父亲1991年加入马航中国,是马航的第一位中国技术员。”今年大四的学生王佳运说。
1989年,马航开设了飞往中国的第一条航线——吉隆坡到广州。之后,马航在中国的业务飞速发展,于1991年设立了马航驻北京办事处,王佳运的父亲就是办事处的第一批员工。父亲在马航负责货运业务,出事前的职务是高级货运经理,马航中国货运的最高负责人。
今年2月1日,母亲告诉王佳运,他父亲在马航年会上抽中了吉隆坡和云顶旅游区的免费名额,问他要不要去。“本来我也会去的,结果3月初学校考试,就只有爸爸妈妈去了吉隆坡。”王佳运苦涩一笑。两周后,2月15日,王佳运在北京西客站坐上火车回学校,父亲一直送他上了火车。这也是王佳运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挥手告别的身?影。
王佳运是北京人,3月8日之前,他是一个无忧无虑,不爱学习的大学生,3月8日之后,王佳运慢慢变得成熟。他成绩不好,没能考上北京的学校,只能远赴四川,读了一所私立艺术院校,学费每年3万。同很多大学生一样,他晚上熬夜,白天逃课睡觉,如果没有发生MH370事件,这种美好的生活还会持续一年。
3月8日早上十点,王佳运躺在上铺用手机查QQ,如果没有其他情况,他打算放下手机,直接睡到下午。这个时候,他接到了北京表哥的电话,告诉他父母飞机出事了。王佳运直接从上铺掉到了地上,他没顾上自己,打开电脑,看到了370乘客名单,找到了父亲的名字。当时,名单上没有母亲,他打电话给表哥,表哥告诉他,他母亲也在飞机上,那份名单不全,表哥已经电话给马航确认过了。
“我一下就晕了,双眼雾蒙蒙的,什么也看不清。”他宿舍隔壁住着辅导员助理,推门进来,开口就问:“马航有一架飞机失联了,能不能问问你爸是怎么回事?”突然抬头看到了满脸眼泪的王佳运,知趣地停住了话头。
那天,同学们凑钱帮王佳运买了下午一点飞北京的机票。当天晚上,王佳运回到了北京的家。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,书桌旁边有一个玻璃柜,王佳运在柜子里看到了一张纸,父亲在纸上写着家里所有银行账号以及密码。
这是王佳运的父母第一次一起坐飞机出行,作为老航空人,他父亲考虑到了极端情况。看到父亲的笔迹,王佳运紧绷的身体彻底崩溃了,瘫倒在地上。
王佳运此后的待遇与其他家属明显不同。他当天晚上就联系到了马航中国区行政主管雷红。接通电话之后,雷红抢先哭个不停,她和王佳运父亲是老朋友,王佳运父亲原定3月10日和她有一个会议,而他,也是马航历史上第一个在自己飞机上出事的高管。
3月11日,王佳运飞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,于次日见到了马航的董事局主席。他没有被安排和其他家属住在一起,而是和机组家属住在万豪酒店。机长哈里的母亲住在他的隔壁,她四处讲哈里给他托了一个梦,“这位大妈说,哈里在梦中告诉她自己在一个很黑暗的地方,非常冷”。
在吉隆坡,王佳运与其他家属几乎没有交集,回到北京后,他也没有加入自发成立的家属委员会。“我的身份太特殊,加入委员会会有些麻烦,另外,对于马航我有自己的考虑。”王佳运说。
在绝大多数家属眼中,马航是一家没有人性,不值得信赖的公司,只要提起,就是一片骂声。但经过MH370事件之后,王佳运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入马航。“马航是一个关联公司,有家族企业的感觉,所有的员工包括家属都会互相照顾。马航员工跟我说,比MH370稍晚半个小时抵达上海的航班着陆后,所有的机组成员是哭着下来的,从机长到乘务。我爸是马航员工,我爸想把我弄到马航工作,当时是非常容易的。有很多一家子全在马航的。”王佳运说。
父亲曾经同王佳运提过为马航工作,但被专业是编导的王佳运拒绝了。3月12日晚上,听着哈里母亲的哭声,王佳运仔细思考了自己的未来。“自己的这个专业很难找到工作,马航起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”
今年7月后,王佳运开始同马航确认工作的事情。9月,马航中国副总裁告诉王佳运,马航目前没有岗位了,他会帮忙联系其他兄弟公司。
“按照中国人的说法,‘尽力联系’就是没戏的意思。”有些着急的王佳运给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写了一封信,通过马航中国转交了上去。
“写的是,马来西亚航空是马中友谊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支架,我不想看到MH370和MH17事件导致我父亲辛苦23年的马来西亚中国航线撤销,甚至中国航线撤销,我也想为此付出一份力,我还给马航重组写了11条建议。”王佳运说,“除了写信,我还有两个渠道,通过联系雇员工会提出我的诉求,因为雇员工会是马航最大的一块心病,影响力非常大,不得已的情况下,我还能联系到马来西亚反对党。”
因自己的特殊身份,从一开始,王佳运就与其他家属保持距离,从丽都饭店到吉隆坡,他几乎没有与其他家属有过交流,到物流园也是偶尔为之。
严格来说,王佳运从未进入过马航家属的圈子。除家属委员会的成员外,人们都不知道,他们中间还有一位马航员工的亲人。在家属微信群中,王佳运也很少出声,他和张婧一样,都不太喜欢大群越来越夸张的气氛——进入10月份之后,家属大群很多人在相互攀比谁遭受的打击更大,这种“比惨”行为,让张婧和王佳运完全无法接受。
也许,青春期的孩子是恢复最快的人群,他们会考虑自己的未来,包括遗产的分配,马航的赔偿,这些都是失独人群想都不会想的问题。
生活的重担之外,父母时常会进入王佳运的脑海。“我以前很喜欢热闹,现在我特别喜欢安静,特别喜欢一个人,哪怕自己胡思乱想,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做出过激的行为。”王佳运说。
同哈里母亲一样,王佳运也梦到过父亲。那是3月28日,“我说你跟我妈在哪儿,他说回家了,我说别乱说,我说我知道你们没回家,快说你们在哪儿,然后他就不说话了。随后我就飘进了机舱,紧急灯光亮着,救生门没弹开,也看到乘务员是慌乱的。有接线短路,冒着火花。父亲在空中飘着,我伸手抓他,但他离我越来越远……”10月10日,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,王佳运小声告诉本刊记者。
到本刊11月3日截稿时为止,已经有四名家属因为衰老和疾病离世。
如今,张婧、王佳运和其他10多名家属已经委托美国Podhurst律师事务所的律师Steven Marks作为其代理,将于近期对马航和波音公司展开法律程序,要求他们公开信息,推动搜索的进展。Steven Marks曾参与多起空难后的诉讼。
但更多的家属还是选择每周一、三、五去马航办公室人要人。“星期五到空港向马航索要亲人。”每周四,栗二友都会给本刊发来这样一条微信。然后,他就坐公共汽车到邯郸火车站,坐最便宜的慢车熬一夜来到北京,再坐三个小时公交车,走一个小时来到支持中心。“我们每星期都来,”他指了下其他家属,“我们再不来,就没有人找我儿子了。”
这是栗二友的战斗,这是马航家属圈的战斗,是这个圈子存在的所有意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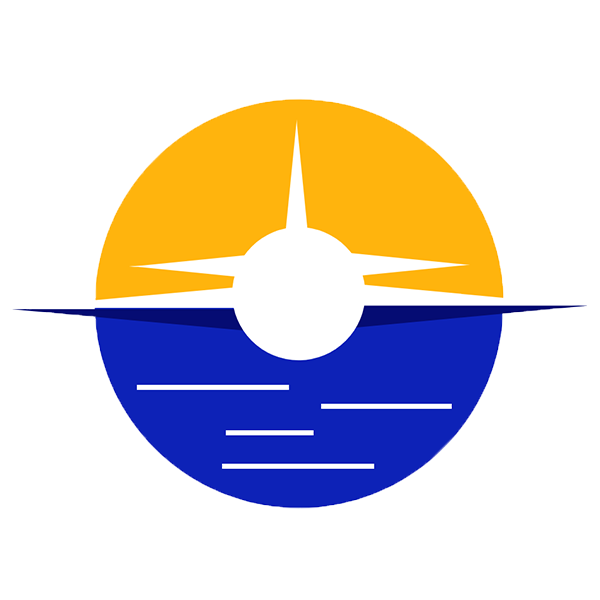


 微信收款码
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
支付宝收款码